2025年5月8日,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发表了玉溪师范学院陈爱林团队与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张喜光、杨杰研究团队的合作研究成果,论文题为Shishania is a chancelloriid and not a Cambrian mollusk(《世山虫是开腔骨动物而非寒武纪软体动物》)。这不仅是陈爱林教授科研生涯中第3次在Science系列期刊发表成果,也是玉溪师范学院首次以主要完成单位身份登上Science。
五亿年前,滇中大地曾是一片汪洋,无数生命在寒武纪时代爆发式诞生。五亿年后,玉溪师范学院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以化石为眼,穿透层层迷雾,揭开地球上最远古的生命演化之迷。
一、科研突围:地方院校的国际前沿研究
1. 世山虫的“身份反转”
在玉溪师范学院古生物研究中心的化石标本盒前,陈爱林拿着一枚化石,“这就是世山虫,过去学界认为它是软体动物,但我们的研究证明,它其实是长着棘刺的开腔骨动物。”他声音带着学者特有的严谨与兴奋,“这枚标本采自昆明禄劝县寒武系第4阶关山生物群,保存了5.1亿年前的动物完整结构。”

这枚化石重见天日,始于2019年。那年,陈爱林带领团队在禄劝县野外考察时,意外在一处裸露的寒武纪地层中发现了它。之后三年,又收集到3枚保存异常完好的世山虫化石。这些化石体表分布着规则的棘刺结构,和已知的后生动物存在较大差异。
但限于当时的科研条件,陈爱林只能将化石小心包裹在棉纸里,存放在蓝色标本盒中。“每次整理标本柜,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看看。”他微笑着说,“就像养孩子,总盼着它长大。”直到2023年,与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张喜光、杨杰团队开展合作,带来了高精度照相分析技术;英国杜伦大学Martin R. Smith博士的加入,又为研究注入了演化生物学的新视角。双方团队对17枚新采获的世山虫标本进行了形态重建和扫描电镜分析,发现其具有辐射对称的外形,表皮存在与开腔骨动物高度相似的骨针排列模式——此前被误认为“刚毛内部生长结构”的组织,实为化石埋藏时矿物质结晶形成的假象。
2025年5月8日,Science正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论文评审专家在评语中写道:“该研究为整合开腔骨动物早期演化模型提供了关键证据,是寒武纪古生物学领域的重要进展。”陈爱林以共同第一作者在Science上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玉溪师范学院的名字,也首次以主要完成单位的身份,与云南大学、英国杜伦大学并列于作者单位栏。这不仅是玉溪师范学院倡导学术兴校以来的重大突破,也是地方院校能够开展高质量科研的证明。陈爱林说,“过去有人觉得地方院校只能做‘边角料’研究,但学校近几年科研上所取得的系列成果说明,只要扎根资源,开放协作,地方院校也能站在国际科研的前沿。”
2. 微网虫“眼睛”之谜
世山虫研究的突破,并非偶然。在Science发表论文的前一年,陈爱林团队刚在Nature(《自然》)旗下生物学领域顶级期刊Communications Biology(《通讯生物学》)破解了另一个寒武纪“明星化石”的谜题——微网虫的“九对眼睛”假说。

微网虫因1991年登上Science杂志封面而广为人知,它最大体长8厘米,躯干两侧长着9对蜂巢状骨板,被部分学者推测为“复眼”,甚至有媒体称其为“九眼怪虫”。陈爱林团队用7年时间,收集澄江生物群10余枚微网虫化石,通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三块正在蜕皮的微网虫化石。“这些化石上,新旧骨板呈叠覆状保存,就像蝉蜕皮时的外壳。”陈爱林指着实验室电脑里的三维重建图解释,“骨板实为表皮角质层硬化物,在蜕皮时期由下层细胞分泌形成。这证明它们是保护躯体的‘盔甲’,不是眼睛。”2024年7月6日,该项研究成果《寒武纪早期装甲类叶足动物的蜕皮》在线发表。《人民日报》以“最新研究破解寒武纪明星化石微网虫‘眼睛’之谜”为题进行了报道,称其“为理解蜕皮动物早期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这项研究的作者名单里,既有法国里昂第一大学的古生物学家Jean Vannier,也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Piotr Gąsiorek博士,还有澄江化石博物馆和玉溪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陈爱林说,“地方院校的优势是离化石产地近,能集合最优秀的一手材料;但技术和理论短板,需要靠国际合作补上。比如法国团队在蜕皮机制研究上的经验,丹麦团队在现代缓步动物发育机制上的专长,都是我们需要的拼图。”
2024年4月18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特种邮票,微网虫作为首枚图案入选。陈爱林为邮票发行和宣传提供了化石最新研究成果,让更多人通过邮票认识了这些远古生命,感受到澄江化石遗产的蓬勃生命力。
3. 从“冷门”到“前沿”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研究者,陈爱林团队的科研之路曾被质疑:“地方院校能做国际前沿研究吗?”但他用成果给出答案:2020年,与合作团队在Science Advances(《科学进展》)揭示寒武纪节肢动物的“演化权衡”;2023年,在Science发表专题评述,质疑“云南虫是脊椎动物干群”;2024年,微网虫研究登上Communications Biology,刺节虫研究登上ELife;2025年,世山虫研究登上Science……
这些成果的背后,是陈爱林扎根地方资源的生动诠释。他说,“澄江生物群是‘古生物学家的天堂’,这里保存着寒武纪大爆发最完整的记录。地方院校扎根于此,完全可以成为国际寒武纪大爆发科研前沿的灯塔。”如今,他的团队与西北大学、云南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实验室里既有自主研发的化石修复土工具(如用篆刻工具改装的微雕笔),也有高大上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还有合作单位共享的高精尖X光计算机断层扫描仪(CT)。
科研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借船出海。2020年,陈爱林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团队合作发表的Evolutionary trade-off in reproduction of Cambrian arthropods(《寒武纪节肢动物繁殖的演化权衡》),就是基于澄江生物群1020枚“卵形川滇虫”化石与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菲尔德瓦普塔虾”化石的对比研究。他说,“寒武纪早期的节肢动物已学会在‘多子多福’与‘优生优育’间优化资源配置——这一机制被认为是节肢动物成功辐射演化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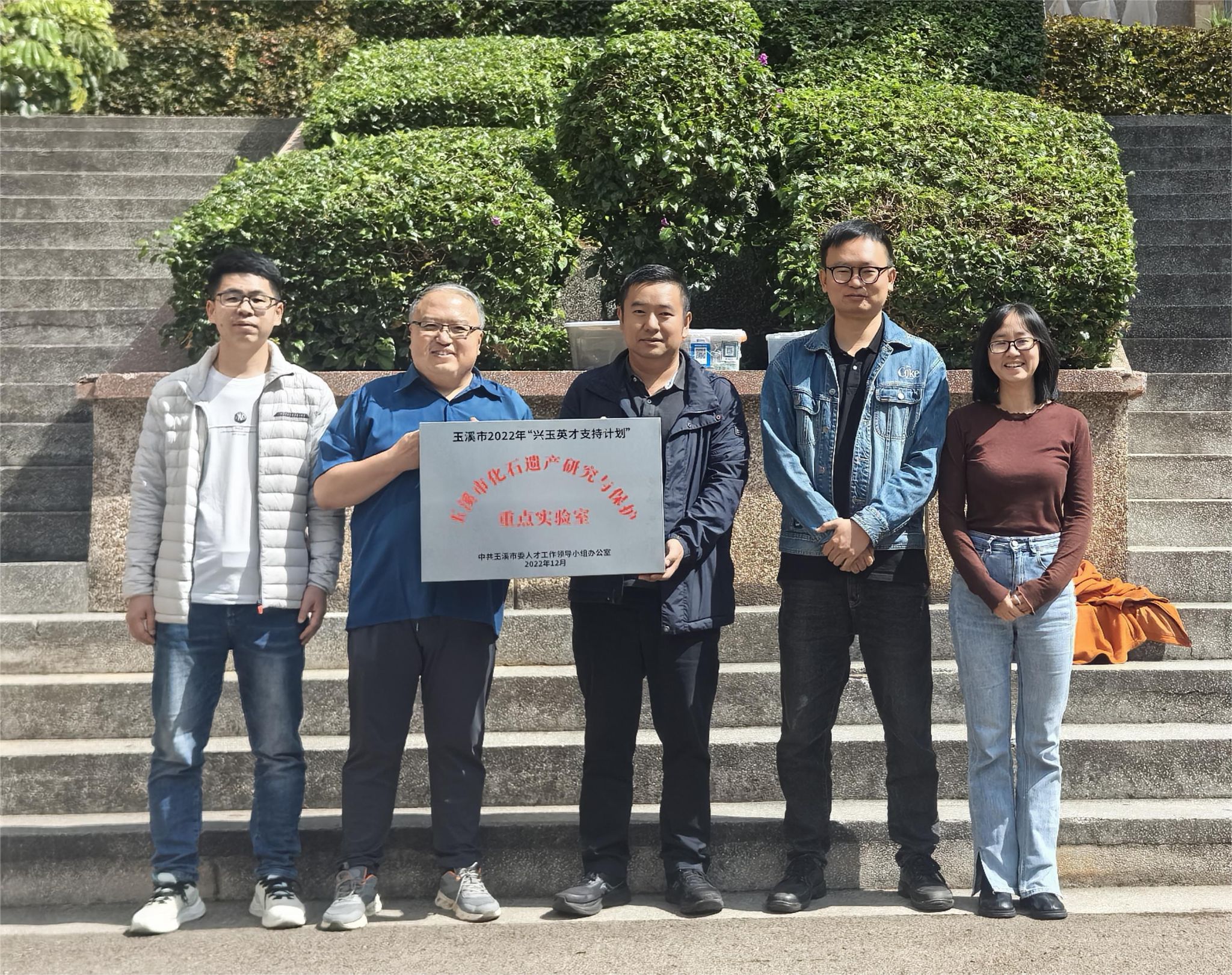
这些研究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62003、42262004、42202003等项目)及现代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大学教育部云南重大生物演化事件及古环境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资助。2022年,在陈爱林积极推动下,与澄江化石地博物馆共同建设“玉溪市化石遗产研究和保护重点实验室”。
陈爱林说,“中国唯一化石世界遗产在玉溪,我们就是要深度绑定这一国宝,围绕化石遗产室内、室外资源保护和科学利用重大问题,通过校内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地理学、法学、美术学、旅游学等专业融合,建设在化石遗产保护技术和开发利用领域具有国内重要影响力的原创基地。建成在化石保护规范、保护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领先的科研创新团队和实验平台,通过与地方资源融合、校政企合作,力争将化石保护学建设成为省内新兴学科,促进云南化石遗产保护和化石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化石守护:5亿年生命遗产的抢救与研究
1. 在科研路上的跋涉
1995年,24岁的陈爱林从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毕业,放弃留在南京的工作机会,回到云南。当时云南没有对口的古生物研究机构,他只好在昆明做了半年多旅行社工作,每天数着日历过。直到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澄江化石的报道,他便立刻辞了工作,坐了3小时汽车到澄江县文化馆报到。
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澄江化石时的情景,县文化馆的角落里,12个绿色铁皮玻璃柜,40余件化石标本,标签是手写的,展柜没有灯光,黑乎乎一片。更让他揪心的是,许多化石的标签写错了年代和物种名,比如一块腕足化石被标成“水母”,一块云南虫化石被标成“蠕虫”。而就是这些化石,遗存着5亿多年前的生命大爆发信息,是全人类的至为宝贵的研究资料。对科研抱有炽热之情的陈爱林,深感责任重大,立刻给在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写信求助,让他们帮忙复印澄江化石研究论文。在周末和假日,他经常步行8公里到帽天山采集化石。那时没有汽车,只能靠脚走,或者搭乘同事的摩托车进山。为采集化石,晴天时,满身都是灰尘,遇到下雨,便是全身泥浆。没有实验桌,就在花台上、窗台上观察标本。没有显微镜,就用放大镜。没有修理笔,就用缝衣针、凿子修复破损标本。一块拇指大的化石,要修半个月,指甲缝里永远沾着化石粉。

1997年5月,云南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在澄江召开保护澄江动物化石群现场会,成立省级自然保护区,陈爱林调入保护区管理委员会。2001年3月,以帽天山为核心的化石产地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陈爱林撰文提出申报世界遗产设想。2012年7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三十六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澄江化石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申遗冲刺阶段的半年时间内,陈爱林几乎熬白了头。在这些澄江化石保护研究的关键节点上,陈爱林都是重要推动者。
2. 与磷矿开采的博弈
守护化石的路上,最大的挑战是磷矿开采。帽天山周边的磷矿曾让山体千疮百孔,化石层被破坏。2004年,陈爱林陪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考察帽天山时,看到山体像被剥了皮,化石碎片混在矿渣里,有的化石被挖机铲断,他当场红了眼眶。
报道见报后,县里某领导找他谈话,“小陈,你端着县里的饭碗,别砸县里的锅。”磷矿老板当面警告,“小心半夜有人拿棒棒敲你。”面对权力和威胁,陈爱林没有退缩,继续向媒体、相关部门反映情况。2004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要保护澄江化石群,保护世界化石宝库,保护这个极具科学价值的自然遗产”。随后,玉溪市立即做出“坚决落实温总理批示,下决心整治矿山,确保世界化石宝库,借此机会加大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和寒武纪公园的建设”的批示,帽天山周边11个磷矿开采点被关停。至此,澄江化石的保护迎来了春天。“那天,我去帽天山,看到挖机停了,矿渣堆开始覆土,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陈爱林说,“现在帽天山的植被恢复了,还种了樱花树,是游客赏春的好去处,偶尔还能在修复的山坡上捡到完整的化石——这是最欣慰的事。”
3. 让化石“活”起来
申遗成功后,陈爱林开始思考如何让化石被更多人看见。他编写的《解谜生命大爆发》《澄江化石地》等科普读物,为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的展陈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2020年8月,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新馆开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寒武纪海绵动物生态复原”展区陈列了陈爱林团队海绵动物的研究成果。在玉溪师范学院,他带领团队开设《世界遗产——澄江化石地》《自然历史》《植物化石鉴赏》《生物进化》4门通识课。“陈老师的课特别‘活’。”上过他课的学生说,“他会举着化石说,‘这是5.1亿年前的邻居,它见证了我们祖先的诞生’,好像在讲一个昨天的故事。”
三、冷门坚守:科学研究中的担当与豪情
从1995年到2015年,陈爱林在澄江基层工作了20年。那是一段孤独但充实的时光。经费短缺时,他炼就了“火眼金睛”,在地摊上寻找化石修复工具和图书资料;行政事务缠身时,他晚上9点到实验室做研究;没有团队支持时,他独自完成化石采集、修复、拍照、写论文。澄江化石研究给了他最大的安慰与馈赠。他经常吟诵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以抒己志。2004年,他发现并命名的“宏大俞元虫”,为古虫动物门建立和后口动物早期体躯分化提供了关键证据,新华社对此专题报道。2010年,他与德国美因茨大学穆勒教授开始合作研究澄江海绵化石,论文发表在古生物专业期刊Palaeoworld和PalZ。2012年,他入选云南省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2013年,陈爱林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当选人大代表,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他说,“我要把基层科研的困难、化石保护的需求,带到全国两会上。”为了把真实情况直接反映到中央领导,他在2013年人代会会议间隙,勇敢走上主席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澄江化石和抚仙湖保护的意义和面临的困难,来自基层的真诚声音,打动了中央领导,欣然为他签名纪念。陈爱林说,“那一刻,我觉得基层科研工作者的声音被听到了!”2015年,他提交《关于进一步提高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博士研究生待遇的建议》,指出西部高校博士月补助仅1500元,难以覆盖基本生活。2017年,这一建议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博士国家助学金标准提高至每月3000元。2018年11月16日,陈爱林入选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和新华公益“平凡化石故事•非凡贡献人物(1998—2018)”全国提名奖,2021年6月9日《人民日报》生态版专题报道这位“自然之子”。
陈爱林除了痴迷于古生物研究和保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在他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排排古典书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他饶有兴致地谈起学生时代求学情况,大学时选修了包括戏剧学、训诂学、中国古代文学等一些中文系课程。上课几乎都坐在前排,十分认真地听讲作笔记。这种不断积淀的人文素养,渗透在他后来的科研与生活中。他写过一首诗:“晨看生命史,思宇宙无情;夜读牡丹亭,慨人间有爱。”他解释,“生命在宇宙中不过一瞬,但人间的爱与责任,能让这一瞬绽放永恒的光芒。”他还写小品文,“闲步校园,虽冷风凛冽,在学堂之翼,但见一泓池塘,波平如镜,池边早树,嫩叶与枯枝齐竞,更有微花,凌寒吐艳。信步山顶,层岩叠嶂,考之源流,寒武之砂,历岁月干锤百炼,已成岩峰。思来岁月久远,学堂千万,大例居城阙之中,喧嚣尘尘,坐寒武而列其上,坚挺如此斯,唯吾校耳。”陈爱林时常把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与专业研究链接起来,用诗化的语言即时抒发,可谓触景生意,思接千载。

“在研究之余,以文学进行调剂,其实是对科学理性思维的平衡和紧张科研的缓冲,从而避免思维局限和极端发展。某种意义上,文理科虽研究领域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陈爱林颇有感慨地说,“文以载道,技以辅文。学文的不妨看点科技书籍,学理的应该多读些文科作品。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时代,人文精神的培育也应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