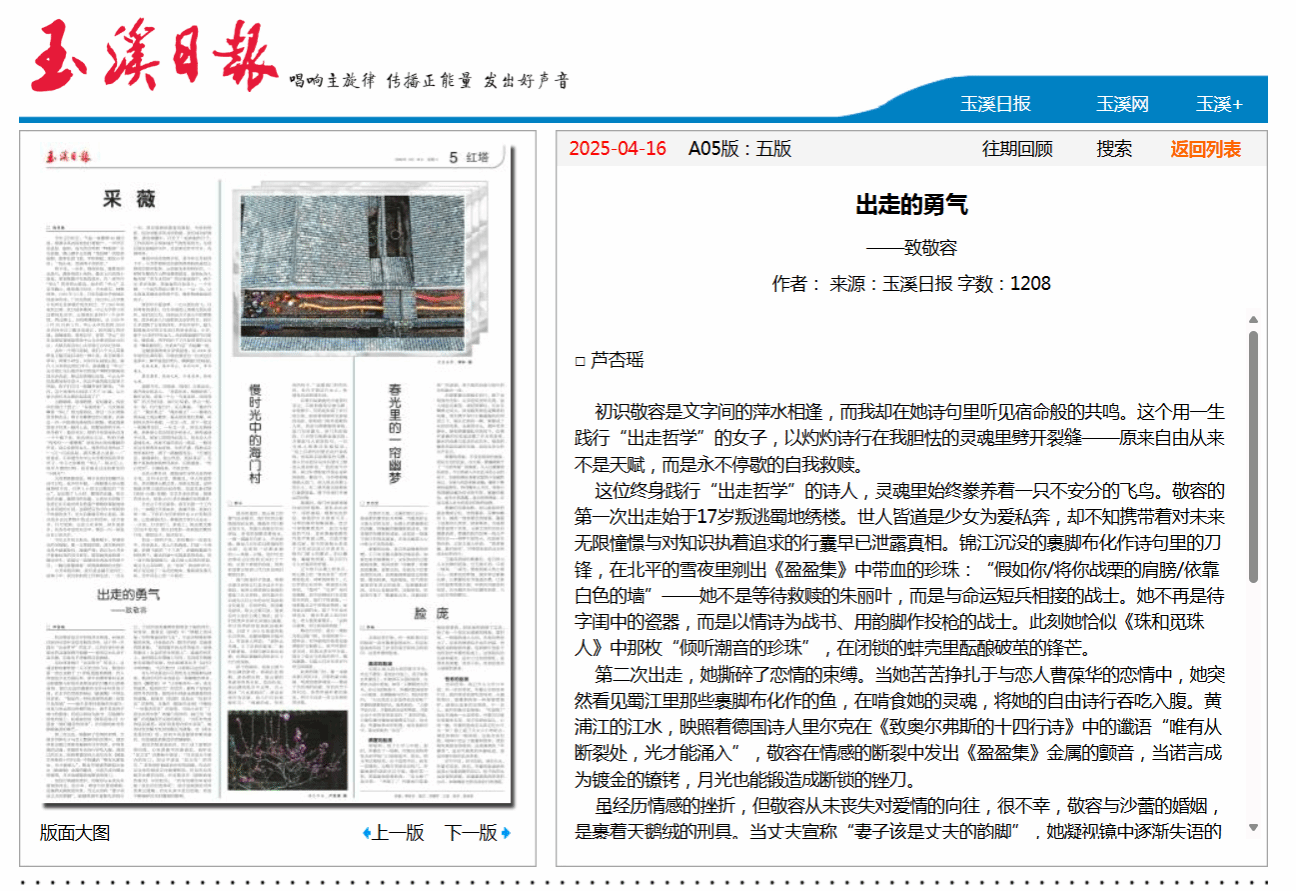
初识敬容是文字间的萍水相逢,而我却在她诗句里听见宿命般的共鸣。这个用一生践行“出走哲学”的女子,以灼灼诗行在我胆怯的灵魂里劈开裂缝——原来自由从来不是天赋,而是永不停歇的自我救赎。
这位终身践行“出走哲学”的诗人,灵魂里始终豢养着一只不安分的飞鸟。敬容的第一次出走始于17岁叛逃蜀地绣楼。世人皆道是少女为爱私奔,却不知携带着对未来无限憧憬与对知识执着追求的行囊早已泄露真相。锦江沉没的裹脚布化作诗句里的刀锋,在北平的雪夜里剜出《盈盈集》中带血的珍珠:“假如你/将你战栗的肩膀/依靠白色的墙”——她不是等待救赎的朱丽叶,而是与命运短兵相接的战士。她不再是待字闺中的瓷器,而是以情诗为战书、用韵脚作投枪的战士。此刻她恰似《珠和觅珠人》中那枚“倾听潮音的珍珠”,在闭锁的蚌壳里酝酿破茧的锋芒。
第二次出走,她撕碎了恋情的束缚。当她苦苦挣扎于与恋人曹葆华的恋情中,她突然看见蜀江里那些裹脚布化作的鱼,在啃食她的灵魂,将她的自由诗行吞吃入腹。黄浦江的江水,映照着德国诗人里尔克在《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中的谶语“唯有从断裂处,光才能涌入”,敬容在情感的断裂中发出《盈盈集》金属的颤音,当诺言成为镀金的镣铐,月光也能锻造成断锁的锉刀。
虽经历情感的挫折,但敬容从未丧失对爱情的向往,很不幸,敬容与沙蕾的婚姻,是裹着天鹅绒的刑具。当丈夫宣称“妻子该是丈夫的韵脚”,她凝视镜中逐渐失语的自己,兰州的风雪裹着炊烟窒息了她的诗行。风雪里,她看见《流转》中“绣绷上的凤凰/突然啄破丝绢飞去”,于是决然撕碎婚姻的丝绢,任丝线化作《陌生的我》里最凛冽的意象:“我的窗开向无言的星空/而我的脚步/永远在陌生的路上”。逃逸的列车上,她用指尖在雾窗上写诗,天亮前任朝露抹去驯服的证据,恰如波德莱尔在《远行》中的呐喊:“任何地方!只要离开这世界”。
在九叶诗派这片以男性为主的精神丛林里,敬容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场静默的革命。她在《雕塑家》中“让形象各有一席:美女的温柔,猛虎的力”的宣言,解构了传统性别符号的囚笼。她的诗行间游走着雌雄同体的魂魄,既能在《抗辩》里发出“咬碎牙齿”的怒吼,又能在《假如你走来》中捕捉“一朵萎去的花”的战栗。当他人还在“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窠臼里徘徊,她已用“捐输”的笔触剖开文明的病灶:“当所有的虚饰层层剥落,将听到真理在暗中哀哭”。她的诗性觉醒与性别觉醒互为镜像,在《老去的是时间》里,时间不再是摧毁容颜的暴君,而是被重新锻造的青铜编钟。
最后的叛逃来临时,死亡成了最精妙的同谋。心电图渐平的曲线里,我听见“恶之花”在静脉中绽放:“自由是永不愈合的伤口,却从中迸发‘恶之花’的芬芳。”若你细听她留给世界的韵脚,你会听见永恒的海浪正冲刷着断锁,听见赤足奔跑在沙滩的闷响,听见敬容在《逻辑病者的春天》中的低语:“所有的痛苦串成项链/挂在世纪的颈项”。那才是她留给世界的真正遗嘱:自由从来不是目的地,而是不断碾碎旧壳时爆裂的脆响。
(原载于4月16日 玉溪日报 第五版 作者系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学生)





